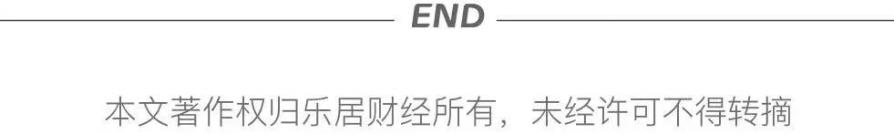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13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72篇原创文章。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
自发布“三条红线”以来,中国的房地产治理整顿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三年来,为了追求所谓的高质量发展,监管层对房地产有“破”有“立”,先是以破为主,后到“先立后破”,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反转。“三条红线”是“破”,“融资三支箭”与“三大工程”是“立”。在当下的破立之间,房价开始出现极其剧烈的调整。如果这个趋势止不住,中国的金融与信用体系将会出现大问题,可以说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间窗口。
这三年多来的房地产转型历程显示,破与立是不对称的两个过程:破如山倒,立如抽丝;破如崩,立如登。基于这种不可逆性,如果不能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就贸然下药方,政策出现重大副作用后就很难有从头再来的机会。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就在于此,作为国家核心资产的房地产体系更是如此。因为它涉及的行业太广,与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阶段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影响。因此当房地产“破”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来的不是钢筋混凝土的“破”,而是信用体系的“破”,国家资产负债表和社会集体心理长期的疤痕。这个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治愈。
日本和美国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破-立”过程。作为一种不动产,期限最长的固定资产,建设年限与使用年限极大的不对称,很容易造成巨大的周期波动,所以房地产周期也被称为“周期之母”。另外一点,作为最佳的抵押资产,房地产周期也创造着信用周期,杠杆既拉大了周期的长度,也加剧了周期的波动。所以,当房地产周期从顶部反转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泡沫和杠杆破裂,房地产危机也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中国的这一轮房地产周期调整与其它国家有哪些异同?触发点都是监管政策的收紧,这一点与日本比较相似。美国更多的是市场的内生调整,当然触发点也与美联储收紧货币有关,但并没有对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直接干预。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周期调整的节奏上——同样是从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从10%左右降到6%左右,日本用了20多年,中国只用了2年多一点。如此短促的时间,很难从政策操作的角度来“时间换空间”,极大的增加了软着陆的难度。
如果说2023年下半年之前,主要是房地产供给侧——房地产民企“三高模式”的“破”,那么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的需求侧——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出现较大的破损。原因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原本被认为永不下跌的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剧烈调整。一线城市的金融属性比较强,比如深圳,当这些城市的房价都开始剧烈调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担心房地产风险向金融系统的外溢。如果房价调整的趋势止不住,不排除会发生越来越多的按揭贷款变成有毒资产从而出现大面积的银行坏账,最终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造成致命性的冲击。
与一二线城市房价剧烈调整可能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相比,三四线及其以下的城市更多的是可能会出现财政危机。因为一二线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相对较低,也有足够的信用能力继续再融资。三四线及其以下的城市地区一方面土地财政依赖度比较高,另一方面过去滥发的债务比较多,尤其是难以算清楚的隐性债务比较高,再融资的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三四线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债务违约、工资与工程款拖欠和由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出现的社会紧张等问题。
如果不能理解房地产对中国这个转型大国的特殊作用,就无法认识到当前房地产问题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从而低估这次大调整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和危机。看上去虽然是房地产周期的剧烈变化,实质上则是最近几十年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这个矛盾涉及到财政、金融、经济、政治、人口、社会等方方面面,可谓千丝万缕、错综复杂。它涉及到一半左右的地方财政收入,四成左右的信贷资产,七成左右的居民财富,涉及到矛盾重重的央地关系,以及由于财富缩水导致的集体心理失落和社会文化变异等诸多问题。可以说,中国这架高速飞行了四十多年的飞机能不能安全降落,就看房地产这个庞然大物能否软着陆。
回顾一下中国房地产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从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世纪初加入WTO到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以世界工厂模式为主导构建了外向型发展道路,是一个外循环逐渐成为主要驱动力量的过程,这个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还算平稳。第二个阶段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新冠疫情危机,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需求整体塌缩,外循环在支撑经济增长上已经难以为继,以房地产+地方基建投资为核心驱动力的城市化进程成为主导的稳增长力量,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逐渐形成,这个阶段是房地产投资、债务和价格狂飙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到现在,“三条红线”触发了房地产长周期的顶部拐点,叠加疫情疤痕效应的长期影响,房地产和中国经济自身的诸多矛盾集中暴露,开启了与日本类似的漫漫去房地产长路。
幸运之处是中国是一个有诸多教训可以借鉴的后发展经济体,事实上最近十年决策层也在一直学习和吸取发达国家治理房地产和债务周期的经验,以便让转型的成本和代价降到最小。先是通过“美国两次大危机的比较”,较早的施行了金融严监管和金融供给侧改革,将影子银行的无序发展扼杀在摇篮之中,以避免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后又吸取日本的教训,通过“三条红线”阻断房地产开发商的“三高”模式,以避免更大的债务膨胀、房价泡沫与不动产过剩。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后疫情时代本已脆弱的预期和信心下,原本对房地产供给侧和金融侧的治理,却极大的打击了需求侧,造成了债务周期下行阶段典型的通缩型去杠杆过程。
当下对政策层来说,“破”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以来一直在“立”。据统计,最近一年各级政府出台的各种稳定房地产的政策超过了100条。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放松房地产的信贷政策,央行也在持续降低房地产贷款利率。最近一段时间在政策上的显著变化体现在央地关系上,也就是中央开始放松对房地产的集中管控,开始放权让各个地方自救。这个变化是巨大的,也是熊彼特说的“财政问题倒逼制度变迁”的典型动力结构。这个结构一旦形成,在当下地方政府的激励升迁模式下,很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之间从过去的“收紧竞赛”转变为“放松竞赛”,毕竟哪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率先回暖,哪个地区的经济就率先复苏。从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角度,也是这个道理。
这些稳定房地产的政策,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立”,更确切的说是纠偏。中国房地产真正的“立”,应该是建立高质量发展框架下的长效机制。当下来看要侧重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借着这一轮深度调整的机会,加快房地产市场化改革,解除掉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还供需给市场,不能浪费危机带来的改革机遇。二是在去房地产化的同时,在更深层面上加快以财税现代化为主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让地方政府学会从建设城市转变为经营城市,从依靠卖地获得的“营业外收入”转变为依靠发展经济获取税收的“主营收入”,相应的从管控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技术性的困难则在破立之间,如何在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前提下实现软着陆,这需要治理层不一般的智慧和魄力,以及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高度共识。
原文标题 : 赵建:中国房地产--破立之间的艰难抉择